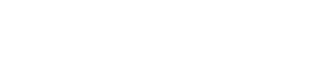殼牌中國集團主席坐鎮解讀:低碳轉型如何重新定義能源公司?

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都需面對的嚴峻挑戰
而能源供應緊張、能源價格飆升
則是低碳轉型中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
減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如何?
減碳與能源安全究竟能否兼顧?
低碳轉型戰略又給能源公司帶來怎樣的變革?
殼牌中國主席黃志昌
與《財經》雜志執行主編馬克
展開了一場深度對話
與你聊聊能源轉型的前沿話題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它不單單是一個供需平衡的問題,還牽扯到地緣政治、烏克蘭局勢的變化。到底會持續多長時間不好說,但是能源轉型與能源安全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從中遠期看尤其如此。
能源轉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源供應更多元化,多元化了,東方不亮西方亮,很大程度上就解決了安全問題。


殼牌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們的能源轉型戰略是一個長遠目標,我們仍然會往這個方向走,沒有改變。
其實,殼牌制定戰略的時候已經做了多方面的考慮。首先,我們看到尊重自然是大勢所趨,必須要提供更多的減碳方案給客戶,要跟社會同步。
更重要的是,無論個人家庭還是商業和工業,社會都要繼續運作。我們會考慮怎么在B端和C端推進“賦能進步”戰略,要在生活、生意和減碳環保之間找到一個好的平衡。
第三,我們的轉型戰略已經考慮了股東的回報。如果做新能源沒有回報,我們可以做若干個示范項目,但沒辦法大規模去做。同時只要市場有需求,我們也會繼續提供油氣產品和服務,不會因為轉型而出現能源供應的斷裂。
2021年跟2016年相比,殼牌自身運營的碳排放已經減少了大概18%,對比2030年減碳50%的目標,這個進度算是不錯的。

天然氣業務是殼牌中國業務的重中之重。生產端,我們跟中石油集團在陜西榆林共同開發了中國第一個陸上天然氣中外合作項目——長北氣田,該項目已有20多年歷史,可以說是中外油氣合作的典范。20多年來,我們累計供氣530億立方米,主要供應華北地區,包括北京。
貿易端,殼牌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LNG)貿易商,也是中國市場里最大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商之一。殼牌去年已經獲得了中國國家管網集團的托運商資格。今年初,我們又跟國家管網集團的天然氣接收站管理分公司簽訂了備忘錄,可通過它們的接收站接卸進口液化天然氣,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直接將天然氣銷售給國內的終端客戶。


這主要還是看市場形勢。短期波動很難判斷,中長期來說,在碳中和目標下,天然氣最后也會跟其他化石能源一樣,降低在能源結構里的比重。但中國在未來10年里,天然氣的需求還是會增加。即便是未來15年到20年,天然氣的需求也不會有很大的跌幅。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進展。
第一,在氫能方面。今年1月,我們在張家口的合資企業旗下的電解水制氫工廠正式建成。這是個2萬千瓦的電解水制氫項目,是我們在中國第一個落地的商業化氫能項目,也是我們新能源業務在中國第一個落地的項目。對整個殼牌集團來說,這也是已建成的規模最大的氫能項目。北京冬奧會交通工具所需綠氫的75%都由這個工廠供應。
第二,充電業務。我去年上任的時候,殼牌在中國只有幾百個充電終端,現在已經超過了3000個。我們除了在自己的加油站加裝充電裝置,也在非常積極地尋找合作伙伴共建充電終端。
第三,碳捕集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業務。各界都在往低碳方向走,但有些領域是沒有辦法完全脫碳的,只能把二氧化碳封存起來。特別是在工業集群里,如果能把需求集中起來,規模足夠大,就可以創造很高的價值。今年4月,我們跟榆林經濟技術開發區簽訂聯合研究協議,將利用碳捕集與封存技術大規模脫碳。6月底,我們跟中海油、廣東省發改委、埃克森美孚集團簽訂備忘錄,在大亞灣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一個1000萬噸碳捕集量的項目,這將是中國首個規模化海上碳捕集與封存集群。


這是跟社會發展同步的。比如,中國2020年的電氣化率是26.5%,到2060年要實現碳中和,電氣化率可能要達到60%,那我們作為能源企業,肯定要加大投資電力業務。

在全球層面,殼牌在可再生能源,特別是海上風電方面已擁有豐富經驗。在深水方面,我們的漂浮式海上風能裝置處于技術領先地位。
我們近期在印度收購了一個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收購完成后,殼牌在全球的可再生能源電力裝機將達到5000萬千瓦,這個規模基本上可以滿足所有英國家庭的電力需求。
貿易一直是殼牌的強項,不單是油氣,電力貿易也是如此。在歐洲我們已經有幾十年的電力貿易經驗,最近幾年在北美也增長迅猛,目前殼牌在北美的電力交易量已經排名第三。
在充電設施建設上,殼牌在全球范圍內已建成9萬個充電終端,比一年前增長了一倍。我們的愿景是到2025年建成50萬個充電終端,到2030年做到250萬個充電終端。
在中國,我們也希望把電力一體化業務做起來,我們會積極探討怎么利用全球技術、全球布局,幫助我們在中國尋求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機會。
在中國從事電力貿易,殼牌是跨國公司里的先鋒,最早拿到售電業務牌照,目前在廣東、江蘇,我們都可以做售電業務。我們尤其重視綠電貿易,去年南方電網公司啟動綠電交易,我們在啟動當天就參與其中。

中國肯定也有愿景,否則全球目標也實現不了。中國市場很大,各地情況不一樣,我們主要是按照城市來布局,哪些城市的電動車應用走得快,我們的充電樁業務也會跟著走得快。
我們首先在自己的加油站布局充電樁業務,加油站這個概念將來會變成綜合能源服務站,或者叫補能站,不光是加油、充電,還可以加氫。這是內生型增長,就是在我們的獨資公司或者合資公司旗下的加油站發展充電終端。
同時我們會用外延式擴張的方式來加快發展速度,比如收購,比如新建合資公司。我們將和比亞迪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建設充電終端,從深圳的1萬個充電終端起步,再向中國其他城市拓展。我們也和蔚來汽車達成了全球合作協議,在國內和歐洲共同建設、運營換電設施。


我們還在跟蔚來探討,我們希望在2025年前能建成100個換電站,具體合作形式還在探討中。

主要問題是綠電供應不足,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完善綠電的交易機制和認證機制,否則客戶第一不知道自己買的電到底是不是綠色能源,第二買了綠電之后缺乏有效的交易憑證,自己創造的環境效益無法轉化為市場價值。把這兩個機制完善了,就能有更多的綠電供應,交易量才能做起來。
在價格上,綠電和其他電力的價差應該充分反映綠電的環保價值,價格到位了,市場就會引導企業更多地生產綠電和交易綠電。此外跨區域的售電現在也不成熟,這也限制了交易規模。
但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中國啟動綠電交易還不到一年,我們對其前景非常樂觀。


殼牌在今年初發布的《中國能源體系2060年碳中和》報告中預測,實現“雙碳”目標,氫能在中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例2030年要達到5%,2060年要達到16%。這意味著我們現在就要行動起來。
沒有經濟效益就無法大規模發展,這個規律對任何新技術都適用,氫能也不例外。供應端要想辦法把成本降下來。第一,綠氫效率最高,也就是用風、光電直接制氫,而非用化石燃料制氫(灰氫),或化石燃料+碳捕集與封存制氫(藍氫)。第二,努力將設備的固定投資額降下來。
在需求端,我們要增加工業的氫能需求,比如鋼鐵行業用氫能替代焦煤煉鋼,比如石化行業用綠氫替代灰氫做化工原料。這兩個行業是最大的工業排放源,一個占中國碳排放總量的15%左右,一個占14%左右,若能實現氫能替代,將大大加速減碳進程。
同時,如果碳排放權的交易機制更加完善,可以把碳價直接算進去,那么氫能的減碳價值就會凸顯,市場對氫能的需求就會迅速提高。
碳捕集與封存技術其實已經比較成熟了,殼牌在西歐北歐、加拿大都有較多運用。在中國,我們近期跟榆林工業園區和大亞灣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簽訂的協議是一個好開端。
討論碳捕集與封存時談及最多的是成本太高,但成本不是技術開發者單方面的事情,碳捕集與封存的成本是一個系統性的結果。如果政府能對更多行業有約束性較強的碳排放要求,那么碳價就會升高,這就等于降低了碳捕集與封存的成本。或者,如果政府一時無法把更多行業納入碳市場,碳價一時無法漲起來,那么政府可以出臺鼓勵政策,例如補貼,來刺激碳捕集與封存的應用。同時碳捕集與封存也需要認證,企業將二氧化碳封存之后,封存量要有權威認證,從而體現其市場價值。碳價越高,碳捕集與封存的價值也越高。


碳市場是一個市場化的手段,是全局性的;補貼是更有針對性的、點對點的扶持。
這兩種手段都需要有,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哪種手段力度更大,取決于政府的判斷,是點對點發展更合適,還是更大范圍推廣更合適。
現在中國的碳價比較低,歐洲碳價大概是中國的10倍。碳價如果能夠體現環境成本,可再生能源投資的回報就會更好,就會有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資。碳價對于綠色技術的落地,有著非常重要的杠桿作用。


殼牌在歐洲有十幾年的碳交易經驗,在中國,我們2014年就開始布局碳交易。除了碳交易團隊,我們還有一個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團隊,這個團隊直接用植樹造林等方式創造高質量的碳匯。這兩個團隊糅合在一起,專業性更強,能給客戶提供更豐富的解決方案。比如,我們能直接給中海油提供碳中和液化天然氣,這些液化天然氣的碳排放,我們已用自有碳匯將其中和。這意味著,我們不僅是幫助客戶進行碳交易,還直接幫客戶完成碳中和,這相當于給了客戶一個打包的碳中和方案。

這方面殼牌在歐洲已有較好的案例。例如在歐洲西北部比利時、德國和荷蘭之間有一個工業集群,區域內的企業對于能源和減碳的需求都一致。我們在那里做了一體化、端到端的綜合能源解決方案:首先,將當地的風能發電直接用于當地的工業用能(多余的風電出售給區域外的客戶)。同時,我們在當地建設了一座電解水制氫廠,將綠氫用于當地工廠,比如鋼鐵廠。對于工業集群區內無法消除的碳排放,我們用碳捕集與封存技術或者碳匯加以中和。
我們希望能在榆林工業園區和大亞灣開發區借鑒歐洲這個工業集群的經驗,實施一體化的工業減碳方案。

一體化的想法可以直接用,具體在哪里建風機,在哪里制氫,在哪里做碳捕集與封存,我們正在與合作伙伴一起研究。
不過,中歐的不同之處在于,歐洲的碳價能夠比較充分地體現環境價值,中國的碳價目前還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需要探討其他的點對點激勵方式。


兩種情況都可以有,主要是看不同的合作方在項目里面有怎么樣的價值。殼牌是自己可以做,但也不排斥合作伙伴。

舉個例子,寶鋼是我們的鋼鐵供應商,我們在全世界的很多項目都需要用鋼鐵。而寶鋼也需要減碳,因為包括殼牌在內,越來越多的客戶需要采購綠色鋼鐵。殼牌可以為寶鋼提供多種減碳方案,可以和寶鋼一起開發氫能和碳捕集與封存技術,這樣我們就變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贏關系。把這個雙邊關系延伸出去,就成了多邊互動的生態圈。在這個生態圈里,不同公司有不同角色,大家可以互相幫助,這是最好的多贏狀態。

我們核心競爭力是有實實在在的技術和產品來讓方案落地。如果你不在能源行業里,本身沒有針對性的技術或者經驗,是不可能提供和我們一樣的解決方案的。比如,殼牌能夠將能效技術、清潔能源供應、碳市場和碳匯交易這三種減碳手段打包成一個解決方案給到客戶。最近我們還推出了一個顧問方案,包含碳足跡核算追蹤、能源需求分析,以及數字化能源管理系統,這是一個一體化的綜合能源解決方案,并且已經有實際落地的案例。
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市場里只有競爭關系。殼牌和數字化科技公司可以相互是對方的供應商。比如,我們可以為數據化科技公司提供綠電,幫助它們減少數據中心的碳排放,對方也可以為我們提供數據儲存服務。雙方可以優勢互補,把減碳生態圈建得更好。

這就是殼牌“賦能進步”戰略的意義所在。
在低碳轉型的變革中
能源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斷被重新定義
殼牌站在能源轉型前沿
將繼續提供更清潔、更低碳的產品與解決方案
向著“到2050年成為凈零排放的能源企業”
不斷前行
注明:本文章來源于互聯網,如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 WICEE 2022西部成都工程機械展 官方網站-中國西部成都國際工程機械展覽會